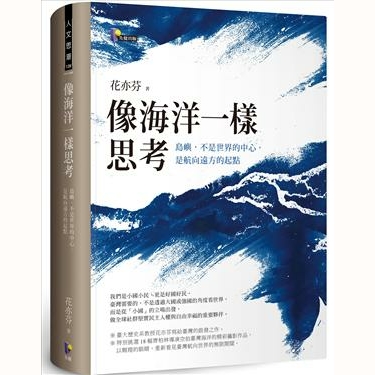摘錄自花亦芬作者緒論——寫給台灣
整個19世紀下半葉,台灣只有在1867年看到英商天立洋行在高雄以新文藝復興風格蓋了台灣第一棟西式洋樓,租給英國領事館使用。兩年後(1869年),蘇格蘭人馬雅各醫師來到台灣,免費為人治病,自此,台灣開始有了西醫。同年,隨著日本政府開放日人自由來台,開啟了日本人來台灣開設西洋料理店的契機。1897年,在今天台北西門町,台灣有了第一家咖啡店「西洋軒」。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喝咖啡已經有超過一世紀的歷史傳統了,但遺憾的卻是,我們並沒有因此發展出在喝咖啡閒談中,喜歡互相激發有創意新思想的討論習慣。
1921年蔣渭水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發表〈臨床講義:關於名為台灣的病人〉一文。他為台灣下的診斷是「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原因是「智識營養不良症」。他的診斷相當切中要點:
蔣渭水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的教育缺乏思考能力的培養,對理性論證、以及世界形勢的評估能力薄弱。可惜的是,他所開出的藥方,希望以一個世代的時間(20年)從幼稚園以迄正規教育、還有圖書館與報社的開設來加強民眾各方面的教育,仍然停留在「受教育」的思考,並沒有針對「國民教育應該培養獨立思考能力」這個關鍵問題來開真正對症下藥的處方。畢竟「受教育」也可以是受洗腦教育,將課堂變成順民養成所。
********************************************
從蔣渭水創辦「台灣文化協會」到現在,即將要滿一世紀。走過殖民、走過威權、經過三次政黨輪替,教育,仍是台灣人感到最無奈的痛。鍾理和在《笠山農場》(1995)這本經典小說裡,也深切地指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對台灣教育而言,威權政治留下來的遺緒清楚表現在「標準答案」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透過好的提問來鼓勵尋找答案」。因為好的答案來自於能先問出好的問題,但威權統治之所以在過去半個世紀能長期得逞,正如專門研究中東歐20世紀極權政治史學者Timothy Snyder所做的精闢分析:「個人總是趕在威權政府發號施令前,就先想到該怎樣做出符合他們心意的事」(individuals think ahead about what a more repressive government will want)。長期浸染在這種習於「自我審查」的習性裡,我們的社會並不看重「探問/質疑」的可貴;我們以為社會內部可以相互取暖的同質性,叫做「台灣主體性」;但卻忽略了,「主體性」本身是一個認知網絡,是一種秩序網絡,只有當我們對自己的認知能夠超越內部的秩序網絡去與越來越多自由民主國家的認知網絡進行有建設性的溝通連結時,台灣的安全才能得到更多的國際保障。因此,當我們在談「台灣主體性」時,千萬不要忽略,要同時能體認到「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也是同等重要。
台灣不曾是世界中心。在17世紀大航海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部在印尼,不在台灣。而在人類史上,會在地圖上把自己畫成世界中心的,除了耶路撒冷外,通常都是帝國。台灣不是帝國,但也不需要因為不是帝國,就以為只能把自己理解成帝國邊陲。
從海洋看台灣,看到的從來就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是的,台灣不曾是世界的中心。只有當我們瞭解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懂得從「小國」的立場重新思考如何走向世界。當我們認清自己是「小國」,也才知道如何打造連結台灣與世界的優質知識,做為我們積極與世界交流的基礎。
台灣對於世界史知識的教育需要脫胎換骨。
我們需要能從自身的歷史經驗,重新思考人類的存在是如何透過不斷地奮鬥;也從世界各地各種歷史經驗裡學會如何轉危為安,而非拿著「帝國史學」或「大歷史」喜歡誇談的「命定論」來進行知識簡化的誤導式教育。畢竟,當歷史學者喜歡當「先知」、而非希羅多德所謂的「探問者」時,歷史學很容易變質為是在為強權政治說項的幫兇。
誠如西班牙反抗佛朗哥威權統治的著名大提琴家卡薩爾斯(Pablo Casals,1876-1973)所說:「我們都是樹上的一片葉子,這棵樹就是人性。如果沒有樹,葉子也無法存活。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良知和善念,根據心中的善念所做的決定,是這個世界最需要的。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需要勇氣。有了勇氣,一個人就可以聽見心中的善念在召喚。」同樣的,學習歷史、瞭解歷史,是為了讓我們對自己所生存的世界具有普世價值思考的現實感,知道如何構築「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關係;而非讓現實感頹鈍淪喪,沒有能力從自身的歷史經驗對過去重新加以提問,也沒有能力眺望遠景,只知活在標籤化論述所構築的刻板印象之中。
1969年,面對一個迴避轉型正義、惶惶不知所終的西德社會,德國社會學家Theodor W.Adorno曾借用哲學家康德的概念──「自己招致的幼稚不成熟」(selbstverschuldete Unmundigkeit),呼籲西德應該盡快打造「幫助國民懂得追求心智成熟的教育」(Erziehung zur Mundigkeit)。因為自由民主的社會仰賴有成熟心智的公民來運作;而當時西德社會尚存的種種威權遺緒須要仰賴有成熟心智的公民來翦除。
台灣雖然有艱困的國際處境,但也是該擺脫對世界局勢向來習於處在不成熟認知的狀態,讓自己成熟起來的時刻了!該是讓我們的國民學習如何獨立思考,懂得用成熟的心智瞭解台灣跟世界各種不同的關係,懂得深謀遠慮,而不要每每聽到「外國」,就只會不以為然地說「但是台灣不一樣」。
「不一樣」是意謂著繼續讓自己遠離國際民主自由秩序的框架嗎?
********************************************
台灣應該要勇敢與國際社會接軌,開朗面向海洋。
健康開闊的台灣意識不是內向性的國族思維有能力打造,也不是歷史悲情打得開局面的。只有當我們決定好好面向廣闊的世界,我們才能在回頭審視崎嶇來時路時,找到可以一起靜下心來撫平歷史創傷的平安與向望。在這個過程中,尤其要看重,確實好好提升台灣的教育,因為我們的年輕世代真的值得。新世紀的台灣意識主要是由他們打出一片天,帶著台灣面向寬闊的世界,開心地與世界交朋友。台灣沒有任何理由再用陳腐的教育繼續絆住他們、用陳陳相因的顢頇耗費他們的青春,讓他們無辜地喪失跟世界最好的國民教育同步的權利。
台灣的歷史教育也不該再繼續用意識形態的對抗來羈絆該破釜沉舟好好推動的歷史教育改革。意識形態有千百種,個人因為不同的背景各有所偏。但是,一個不願意好好打造普世價值的社會、一個不願意好好打造普世價值的國民教育,即便社會內部自己喊得震天價響、熱血沸騰,到頭來,終究成空。
好的歷史教育在於引導去培養好的批判性思考,誠如德國著名的歷史學者Wolfgang J. Mommsen所說:
民主自由與人權價值是台灣最好的安全保障。有堅定的價值理念,才看得到逐步落實夢想的方向。有夢想,才走得遠;也才能將世界的豐富美好帶回原來啟航的地方。
賦予台灣民主自由無盡續航的潛能。
給台灣年輕世代航向美好未來開闊的空間與向望。
台灣雖小,因開闊而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