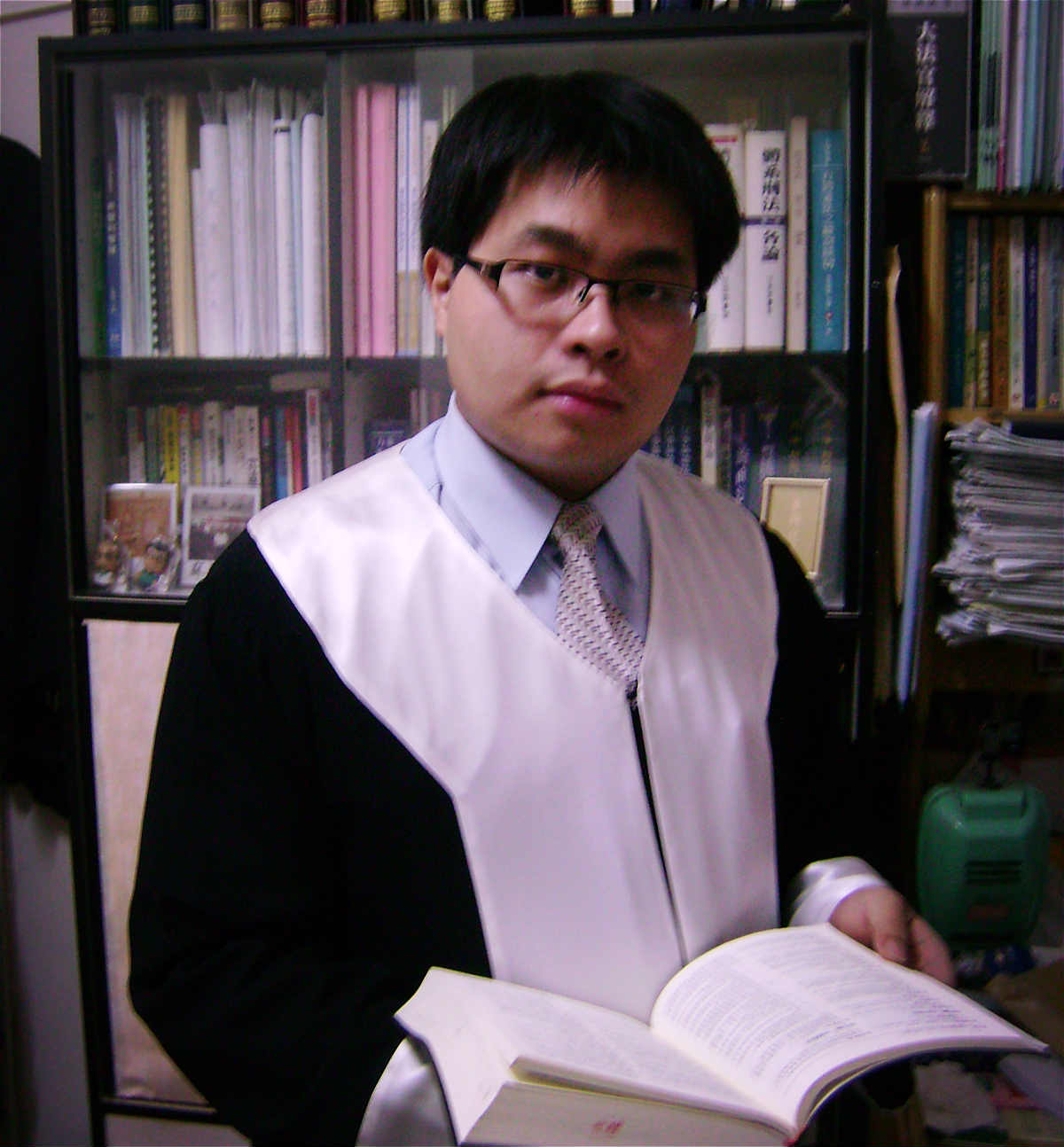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警察是偵查輔助機關,警察所可以進行的蒐證行為,以法律有明文授權為限,也就是說,如果法律沒有明文授權警察得廣泛以「人臉辨識系統」進行蒐證,但警察卻擅自進行,就是當然的違法行為。
高雄市議員郭建盟在質詢及媒體投書指出,「警方在學運期間大量使用DV錄影蒐證,再透過連線身分證、護照相片資料庫的M-Police人臉辨識系統比對找出學生身分,這套系統更載入iPad,讓警員可以隨身攜帶,輕易透過拍攝民眾照片後上傳比對」。如果警政署確如民代指控,在未有法律授權的前提下進行「人臉辨識」,則該等行為當然違法,警察對於違法侵害人民「隱私權」的行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法院對於違法取得的刑事證據,也應認定不具「證據能力」。
警察能否隨意取得個人照片進行比對,涉及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大法官在釋字第603號解釋很清楚指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簡單的說,警察進行「人臉辨識系統」的蒐證行為,當然涉及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故警察如擅以「人臉辨識系統」對人民進行蒐證,當然侵害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之隱私權。
台灣是民主法治國家,政府可以限制人民的隱私權,但必須要有法律明文規定作為前提,這也是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的基本要求,因此大法官在釋字第603號解釋指出「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所以警察能不能用「人臉辨識系統」進行廣泛地蒐證,涉及人民隱私權之限制,警察有義務提出其法律依據。
然而,遍查刑事訴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律,均沒有授權警察得以「人臉辨識系統」進行廣泛蒐證的法律明文,換句話說,警察在沒有法律明文授權的情況下進行「人臉辨識系統」蒐證,當然牴觸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保障人民「隱私權」意旨,違反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即屬違法違憲之行政行為。
基此,警政署對於民代質疑警察以「人臉辨識系統」進行蒐證,自有義務對社會說明,警察有無該等行為,又執行的法律依據為何?如警察確以「人臉辨識系統」對學生進行廣泛蒐證,依據國家賠償法規定,警察不法侵害人民「隱私權」,人民當然可以請求警察負國家賠償責任;另依刑事訴訟法,警察違法取得的刑事證據,法院也應認定不具「證據能力」,並排除因此取得的相關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