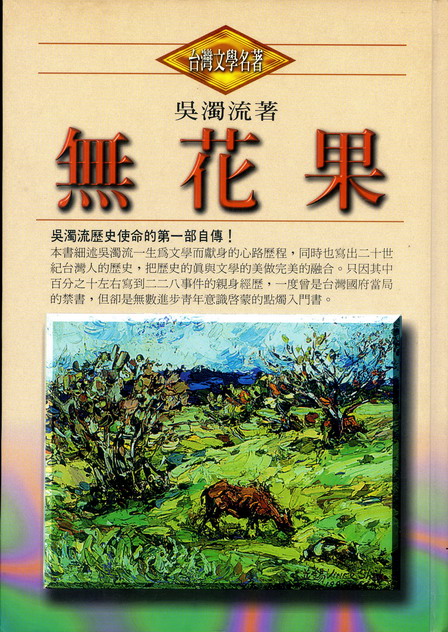《無花果》一書,雖說是吳濁流所寫的一本自傳,但我們不能把它當作普通的傳記文學來看待。書開頭的第一章裡,它就坦誠地寫道:「回顧過去自己走過的人生路程,感其失敗之多,實不勝驚異。這種情形,像回憶錄似的東西是不能寫的,寫的話,自己的醜陋的姿態,會夾在中間顯露出來。」由此我們不難推斷,寫自傳,把自己赤裸裸地呈現在大家眼前,實非吳老所願,更非是他寫《無花果》的初衷。「回顧我走過的人生路程,雖然平凡,但也逢上了幾個歷史上的大事件。第一次大戰、台灣中部大地震、第二次大戰、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等便是。」面對二二八事件,在擔憂「將來這個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的情形之下,他才在寫與不寫的惶惑中斷然執筆。
台灣人意識的成長
「要瞭解這個﹝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無論如何,非探求其遠因不可。」由此,他才提出了「究竟台灣人是什麼」這個問題,為二二八這段史實,掀開了最嚴肅的序幕,也同時為「台灣人意識的萌芽、成長及至定型的追索探討,提出了最深入、最清晰獨到的描述。
吳濁流並不否認「台灣人的大部分是漢民族的後裔」,但是,「台灣是台灣人所開拓的,絲毫沒有借用任何外來的力量。然而清朝卻絲毫不考慮台灣人的意志,擅自把台灣給了日本」,此舉激發起台灣人長達五十年毫無間斷的抗日活動。吳濁流認為,當時的抗日活動,完全出自於一種「自發性」,既沒有橫的聯絡,也沒有縱的系統」。他進而以鄉人文進伯,對這個論點作了相當動人的描述:「‧‧‧文進伯,聽到日軍來了,拿起種田人切田塍的劈刀,和村中的壯丁們,一起馳赴涼傘頂。但是,當日軍打來的子彈,飛過他們的頭頂時,他驚異之餘,狼狽地逃了回來。這成了村中的笑話流傳下來。」「但是,我所知道的文進伯‧‧是柔順的壯年人,是勤勞的農夫。簡直不敢想像,那樣馴良的伯伯從前曾反抗過日軍。」由此,我們不難察覺,保衛自己的鄉土,乃是出於本能。這種愛台灣、愛鄉土的本能,正是所謂「台灣人意識」的原始雛型。
究竟台灣人是什麼?
鑑於自小由祖父一手帶大,吳濁流一生的為人思想,可說受其祖父的影響甚鉅。早期所謂的「祖國情懷」,亦可說是完全秉承自祖父的「抽象的、觀念型的感情」。在成長的過程中,其「客家人」的身世,也曾佔領過他尋求自我身份﹝Self-identity﹞的思想領域。但是這種「客家人意識」,在開始當教員,遭受到日本人不平等的待遇與欺壓之下,就完全與「台灣人意識」融合為一體了,這可說是受到「命運共同感」的驅使。然而,處於殖民地的台灣,在「面對日本的強大武力,與台灣人等於是雞塒裏的雞而已,註定無能為力」的情況之下,吳濁流對所謂的「祖國」,仍然存有某種程度的幻想,這倒可解釋為「望梅止渴」,或「大海中抓住一根稻草以避免沉溺」的心態。
等他四十二歲到了中國大陸以後,他心中承襲自上一代的「祖國情懷」,才開始逐步地瓦解分裂。及至台灣光復,經過二二八事件的摧殘,這個「祖國夢」,才全然壽終正寢,而道道地地的「台灣人意識」,也才得以完整地落土定型。這種於輾轉反覆的游離,逐漸找到「自我身份」的過程,相信諸多上一代、這一代,甚至下一代的台灣人,均可自其中找到自身活生生的印證。
走上文學,事出偶然
如前所提及的,吳濁流一生的思想行為,深受其祖父的影響,他人生所追求的一個理想,就是渴望有一天能如祖父一般,持著超越現實的態度,中庸的處世方法,過著陶淵明式「晴耕雨讀、飲酒吟詩」的隱蔽生活。然而,人生的際遇往往事與願違,經過現實生活百般的折騰,他這個夢想終其一生均不得實現。
吳濁流之走上文學的道路,實際上是事出偶然。他對文學方面的興趣,可說啟蒙於一位「年輕貌美、天真爛漫」的日本女教師,在她的鼓勵之下,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水月》才得以問世。 然而隨著女教師的離去,他的文學熱倒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地一蹶不振。往後受到了一位日本教授的百般鼓舞,他才又回到了文學的領域。
歷史使命的呼喚
於《無花果》這本書中,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平凡的人,具有太多平凡人的缺點。雖說寫《無花果》,把自己的醜態公諸於世,實非其所願,但是基於歷史使命的呼喚,他於三思之餘,還是毅然決然地提筆。以一個平凡之人,和自認極其平凡的一生,來對台灣的史實,作出最坦誠、最忠實的交代。如果由小說家敏銳的嗅覺評斷起,吳濁流這本自傳小說的成功,已是毋庸置疑了。
佛桑花與無花果的抉擇
本書中,吳濁流把自己形容成「始終只是個中間份子,不偏不倚的隱藏在灰色裡,永遠不平不滿,不能從牢騷感情脫出一步。」他雖自認本性相當怯懦,缺乏以卵擊石當烈士的勇氣,但是做為一個有良心、有思想的知識份子,內心的衝突與掙扎,不曾為他帶來片刻的寧靜。縱然如此,他卻自始至終執守著做為台灣人的本份。在台灣文化最青黃不接的時候,在無法與邪惡的統治者以武力對抗之下,他責無旁貸地從事著承襲香火的文化運動。他寫道:「我開始在檢討已逾不惑之年而仍經常在迷惑中的自己的人生觀。我覺得不應該再好高騖遠,寧可採取莊子所說的泥龜。或者就像無花果一般,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開花吧。」在《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他更進一步地闡釋:「‧‧‧一切生物都有兩種生活方式,例如佛桑花雖然美麗,但花謝後卻不結果;又如無花果雖無悅目的花朵,卻能在人們不知不覺間,悄悄地結起果實。」其絃外之音,無異在指出人的一生,也可能有兩種不同的方式。有的人雖轟轟烈烈地過其一生,死後卻沒有留下任何值得記取的事蹟;有的人雖平凡無奇,固守本份地過著毫無絢麗光彩的一生,但不知不覺中,卻為後代留下了豐碩的果實。於官祿、權勢與財富等的追逐中,每個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標可能大相迴異,但其終點卻殊途而同歸地在於「自我信心」與「自我價值」的肯定。吳老經過一生的掙扎,到了《無花果》這本書完成之時,對於自己平凡的一生所塑造出來的成果,可說已感到相當的欣慰,相信這就是他以《無花果》來為其自傳命名深意之所在。要如佛桑花一般,或如無花果似地過其一生,相信這也是每一個人、每一位台灣人,以及所有的人類所面對的一項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