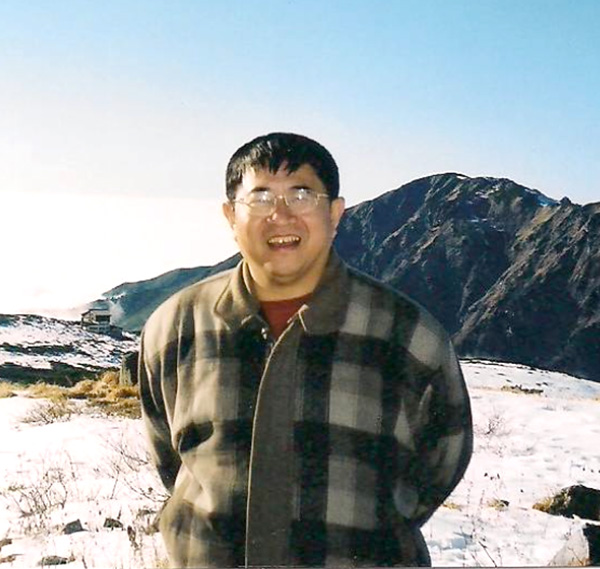理性與感情
我是一個理性的台灣獨立主張者,我可以跟任何不同的主張溝通,只要對方願意誠摯地跟我溝通的話。或許因為自己太過理性,所以自己寫出來的文章總是論理的,而且我也相信透過理性的溝通,才有可能讓不同的意見達成對國家認同的共識。但是,無可諱言的是:我成長的故鄉孕育著我對台灣的愛,這是使我成為一個台灣獨立主張者的最大原因。隨著時間的經過,台灣已經漸漸成為絕大部分台灣人的第一故鄉,或許透過感情面的共感可以讓台灣人培養出共同的感情,使大家產生彼此是兄弟姐妹的一體感。芬蘭的音樂家西貝留斯(Jean Sibelius)所寫的芬蘭頌(Finlandia)其實就是透過樂曲激發出芬蘭人的共同感情,台灣人如果能夠創造出影響台灣人的感情靈魂的創作,喚起大家對台灣的愛,或許我們將更快走上新的獨立國度。
對童年與故鄉的歌詠
我們幾乎可以說:任何人對故鄉的感受絕對是感情的,而非理性的。而故鄉與童年其實是無法分開的。有一種無法用言語講清楚的感情、感覺,就好像呼吸隨時會跟隨著你一般,你不會特意去窺見它的存在,但在你寂寞的時候,在你受挫的時候,在你見景思情的時候,它會像泉水一般不斷湧現,讓你噙著眼淚,用著兩眼看著在自己腦海中所不斷浮現的光景,那就好像是鄉間的小路引著你回家,而在剎時間看到母親坐在家中等著你回來一般,也好像是在夢中、在恍惚中看見幼兒的朋友在榕樹下玩捉迷藏一般。
但是當你懂事以後,那種感覺、那種感情似乎已很難湧現,它好像被壓在看不見的潛意識深淵裡,或許是懂事讓你把世間顛倒過來看的緣故吧。天真無邪是不懂憂愁的、是只有歡笑的,在天真中所出現的大自然,它是純潔無垢的,這個沒有自我的純潔的心,就在不懂憂愁的歡笑聲中,與玩伴們盡情地把那時間與週遭的景象咬碎,然後將之吞到肚裡,化成自己的血肉而變成腦海中的一部分。雖然體內不斷進行著新陳代謝,但卻瀉不掉那腦海中的小細胞。
長大是件痛苦的事,它讓你突然知道有個自己,是會與別人比較的自己,它會讓你原本看到的世界突然變成是一個失去無憂、失去歡笑的世界,一下之間,舊日那個沒有自我,只是天天歡喜打鬧的心情突然消失了,所剩下的就只有腦海中所儲存下來的那些小細胞。拖著歲月痕跡的人們離鄉背井跑到異鄉賺食,面對著世事多變的社會,卻常常會在種種偶然的機緣中,被一條看不見的細小的絲線牽引著,讓我們在偶然的機會與舊日的遊伴相遇。或許與遊伴彼此之間的話,都是一些打不到心底的話,但是在對談的偶然機會中,所有的遊伴都會很自然地講出或唱出或畫出他腦海中脫離不去,但是卻是與自己相同的景象。因為他的故鄉其實就是我的故鄉。
故鄉的擴大與想像共同體
即使不是自己的兒時玩伴,但他們卻是和自己有著相同成長經驗的人,這或許就是安德生(Benedict Anderdon)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當你在思念自己的童年與故鄉的時候,他也用著相同的思念在想著自己的故鄉與玩伴,這或許就是我們為什麼都是台灣人的緣故吧!
當自己離鄉背井與沒有相同故鄉經驗的他人相遇時,雖然彼此之間很難產生相知相遇的感情,但是當聽著大家所共同熟知的歌曲,看著大家所熱愛的作品、戲劇,講出能夠相知的話語時,這些不就是透過傳播、教育等的力量讓我們雖無相同的故鄉經驗,但卻有著共同的故鄉背影的緣故嗎?日本二戰前的文學家石川啄木寫過一首詩歌:故鄉的口音,是多麼地令人懷念啊!在車站突然聽到那個口音,我就推開人群跑過去找(ふるさとの訛(なまり)なつかし 停(てい)車(しゃ)場(ば)の人ごみの中(なか)に そを聴(き)きにゆく)。
當我們在思念自己的故鄉而流淚的時候,有多少的人不也是在思念著自己的故鄉而流淚嗎?而在對土地的共同感情上,別人的故鄉不正也是自己的故鄉嗎?
喪失故鄉卻找不回故鄉的台灣
或許從童年與故鄉可以讓我們找到一個讓政治對立減緩的線索,人或許是如同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所說的一般,沒有長大的人們曾經是處在牧歌式的時代,是和平相處的,但是那個能力在我們長大以後被遺忘了,在以滿足慾望為基礎而產生的工具性理性之下被壓抑就不見了,但是那個能力是本來的自我所具有的能力,那個能力是使和平持續最大的來源,只是我們好像不太會將之加以利用。台灣人吵了老半天,每天都充斥著假新聞,一切的作為都只是為了追求權力,也沒有辦法真正解決許多問題,結果卻忘掉了本來的自我就是解決問題的根源。德國的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曾用「故鄉的喪失」來描寫現代文明的迷失,這也是台灣社會政治紛擾與不斷鬥爭的寫照,但是這個故鄉不正是童年時期的自我嗎?如何找回那個本來的自我呢?或許解決台灣的問題,就在台灣本身。當對台灣具有敵對意識的一輩逐漸凋零時,從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感情來重新建立我們的共識是會比較有效的。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