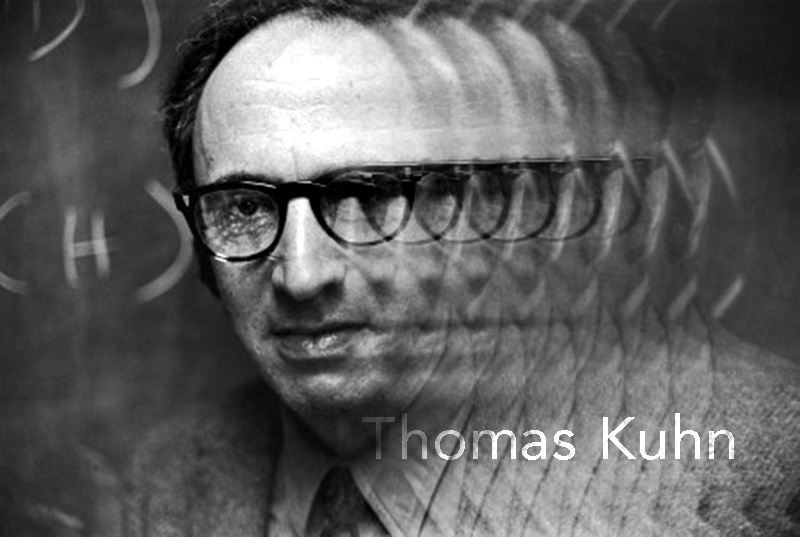那麼,「到底什麼是科學事實呢?」
難道,真的存在一種異於科學事實是客觀且價值中立事實的觀點嗎?
是的,的確有很多哲學家、科學家與社會學家,對「什麼是科學事實?」這個看似單純的問題,抱持一種會讓一般年輕涉世未深的科學家深感驚訝與困擾的觀點。
在一本著名的哲學教科書《哲學概論》(About Philosophy)中,哲學家Robert Paul Wolff說:(以下譯文修改自郭實渝等人的譯本)
在科學中,如何確定某件事是事實?對局外人而言,也就是並未真正加入現代科學研究的人,會自然而然地認為正確答案應該是:一項對世界的論述要被大家公認是科學事實…要能透過在同一領域內,從事獨立研究的若干優秀的科學家,個別的觀察、計算、和理論詮釋來加以證實。
但是真實故事卻完全不是這回事。真實的情況似乎是這樣的:科學家以時下公認恰當的形式來撰寫研究報告(恰當的註腳方式、正確的口音及語言、做為研究人員的證明文件等。)並將論文提交給一份被認可與常被引述的期刊-這些刊物定期出刊而且受到科學家的尊崇,這些刊物只刊載那些經過其他可敬科學家匿名審查並決定是值得刊登的論文。
當這篇文章出版後,它可能被同一領域內的其他研究者所引用,或許也可能未被引用。如果它未被引用,其中的論述也就沒有能見度,就無法成為科學事實。如果它被引用了,這些命題就有機會成為科學事實…
如果未來的研究…一再引用原論文,那就建立了該論述的科學事實的地位,以後即使其他科學家在引用時,或許不會再標明原論文出處,但實際上已經成為他們自己實驗或分析的基礎了。
讀者從這種描述可立即看出,到底某些事情是否能成為一項科學事實,完全是社會約定成俗的。除非被科學社群所接受,即透過被引註…最後被認定為科學事實這條途徑之外,並沒有其他的方式。但是飛機會飛,燈泡會亮,心臟栘植手術有效,以及原子彈確實會爆炸!這些都是明顯的事實,而不是經過人為約定、協議、或者社會決定才成立的。
…但是原子彈會爆炸的事實,並不能解決原子物理學上的爭議,就像十六世紀的水手雖然能靠著天上的星辰找到了回家的方向,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天文學理論是正確的。
這種「科學事實是一種社會約定成俗的結果」的論述,所對應的科學哲學的概念,稱為「社會建構論」。社會建構論的科學哲學觀點可回溯至,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湯姆斯‧孔恩。孔恩在其銷售數量破百萬冊的科學哲學的經典之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書中,提出「典範」(paradigm)、「常態科學」與「科學革命」等概念。簡單的說,典範是指一個科學社群的科學家所共同接受與推崇的分析架構(或方法或工具),一般科學家所進行的科學活動叫做常態科學活動,常態科學活動是一種解謎活動,或是一種塞框框的活動,就是強將一項問題硬塞入一個固定框架(典範)中看看會擠出什麼花樣的研究活動。科學革命則是尋求新典範以解決舊典範所不能解釋的自然或社會現象。因此,科學革命是一種典範的移轉。只是孔恩強調一種典範就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科學家皈依不同的典範,只表示科學家以不同的方式、角度或眼鏡看世界。典範移轉只是看世界方式的轉換,並不表示科學的進步。「科學革命不代表科學進步」的觀點聽起來非常奇怪,但孔恩強調科學史上出現太多曾被普遍相信並推崇為真理的學說,後來都被掃進歷史的灰燼中。你哪知道,今日被尊崇為真理的理論,明日不會也被掃進歷史的灰燼中呢!
孔恩開創性的科學哲學觀點,一方面扭轉了由Karl Popper證偽論所主導的科學哲學的主流觀點,另一方面演化出科學事實是一種科學家約定成俗的「社會建構論」的新論述。「社會建構論」強調科學研究也是一種人類的社會或文化活動,其本質跟其他人類活動如打橋牌、打籃球沒有兩樣,種種人的因素(主觀性、權力結構、私人慾望、結黨營私、排除異己、同類相聚、互相提拔、利益共享…)好的或壞的人類本性都會進入科學活動之中,因此科學社群所折衝協商出來認定「什麼是科學事實」的遊戲規則或成功標準,有可能可以順利客觀地篩選出自然規律而成為公認的科學事實,但也很有可能透過人定標準所過濾出來的科學命題不是自然律,其實只是權力遊戲與利益分配運作的結果罷了。這等同於是說,誰掌握了權威期刊,誰就能左右科學事實。換句話說,在國際學界中,身居國際學術殖民地的台灣的一位學者,可能就像一位穿著土耳其服裝的天文學家,他的研究的重要性與可信度可能會先被打一些折扣,而且可能是相當慷慨的折扣。
當然,有些科學家對「社會建構論」的科學哲學觀點感到非常反感,尤其是非常重視實驗證據的物理學,知名的物理學家1979年諾貝爾獎得主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在《科學迎戰文化敵手》(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書中,就非常生氣地強烈反彈說:「我可不是騙子!」。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孔恩也是一位物理學家,他所討論的對象正是物理理論。
科學的「社會建構論」的主要教訓是,被科學社群所認同的科學事實不見得是真的科學事實。簡單的說,愈有能力(技術與傳統)以重複的實驗與田野證據來檢證或否證其科學假說的學門,其學術社群所篩選出來的科學事實愈可能是真實的;愈沒能力(技術與傳統)以重複的實驗與田野證據來檢證或否證其科學假說的學門,其學術社群所篩選出來的科學事實愈可能是虛假的。
如果在嚴謹的物理學中有些理論可能只是社會建構的不切實際的理論,那經濟理論會呈現怎樣的風貌呢?間接透過上述「什麼是科學事實?」的討論,可幫助我們在未來審視「什麼是經濟學事實?」時,拓展我們視野的廣度,也強化我們思維的深度。
究竟經濟學(經濟學事實)可能只是不切實際的「社會建構論」的產物,僅是經濟學家們自己玩出來或慢慢演化來的「虛擬遊戲」,或是甚至現代主流經濟理論好像可以歸類為只在意預測與解釋能力高低而存心不管且避談前提假設的真實性與合理性的占星術呢?還是,口口聲聲說「現代經濟理論怎麼說」的經濟學家絕對不會是一些有意或無心的騙子。並且,現今主流的經濟理論早已捕捉到經濟現象如何運作的「自然法則」了,經濟學其實已經是一種真理,已經是一種客觀的和價值中立的真理了呢?
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兩種極端相異的論述呢?同樣的,我希望能利用此園地,在未來的日子裡,跟你講很多有關經濟學與經濟學家的故事,讓你能慢慢能形成你自己的看法,得出你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