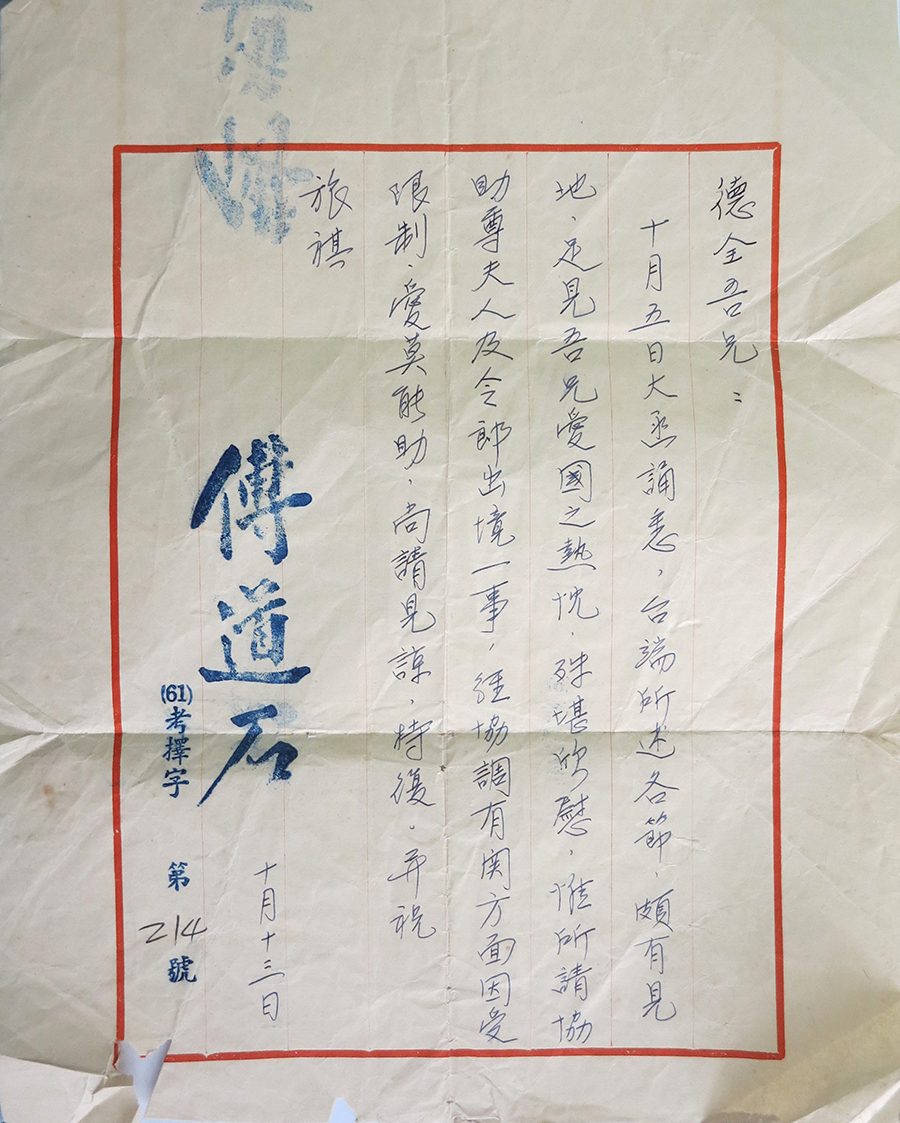相關系列:
【重生與愛】系列四 黑夜漫漫無時盡 ― 衛德全訪談紀錄(上)
【重生與愛】系列四 黑夜漫漫無時盡 ― 衛德全訪談紀錄(中)
回想起過去 每天都在做噩夢
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臺灣比較民主,我覺得對我是有改善一些。兩千年陳水扁上臺後,有一段時間好像改善很多,社會上的人也不會怕被抓。但是到馬英九上臺,好像國民黨又回過來了,像(二○○八年)大陸的陳雲林來臺灣,馬英九不讓住在臺灣的人拿自己的國旗,而且還要動用警察暴力對付人民,這點我就認為國民黨又回來了。我對國民黨完全沒信心,雖然沒有來抓我,但是我的精神、靈魂好像又被抓去了。所以晚上我一定會作噩夢,我就怕國民黨,國民黨對我的傷害很大。可能是因為當時抓越多,消滅共產黨的希望越多,他們對不管是外省人、臺灣人,寧錯殺一百個無辜的人,若裡面有一個共產黨就回本,而且情治人員(特務人員)捉人還可以有高額獎金領。所以我認為這個社會真的很不公平,也沒有人性和公理正義。

2009年1月19日,綠島人權園區舉辦第三屆青年體驗營,衛德全(右)與難友蔡焜霖(左)合影。(曹欽榮 攝影)
有時候越想我越傷心,一想晚上就睡不著覺,整個人好像快瘋掉。所以,我盡量不去回想過去,把它忘掉。這麼辛苦,我們再不講話,歷史就會埋沒。我被抓時二十歲,比我年紀大的那些人都沒有機會講話了,有機會講話的是現在我們這些七、八十歲的人。再過幾年我們可能都要離開,過去的歷史可能就要埋沒在黑暗裡,所以這六、七年我才答應接受採訪、參加受難者的活動。
幾年前接受採訪之後,講一講好像睡得比較好,過幾天就不行了。我到底該講嗎?講有用嗎?慢慢的回想起忘記的過去,每天都作噩夢。這是沒親身經歷的局外人難以體會的情境。
期待公義、自由、人權的社會
十年牢獄之災與出獄後的精神煎熬,我只有一句話:「我要活下去!」這樣的信念支持著我。我知道像我一樣被抓、被判刑的人,有很多人不明不白就被槍決了。早在二二八發生時,更多的人是先槍決、後判刑,有的根本不用判刑,是暗殺。林義雄家滅門案、陳文成枉死案可證明,大部分都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與社會菁英。反觀自己,既沒被刑求,出獄後又順利復職,是該好好的珍惜。但是,我對當今的社會政治局勢感到很憂心,因為臺灣若與中國統一,中國的專制、非人道等社會控制手段將會影響臺灣。所以,我期許臺灣人(在臺灣有戶籍,在臺灣生活,在臺灣生存的人)要團結,不分族群,一起為臺灣的後代與未來著想。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希望要有一個公平、正義、人民有尊嚴、社會和諧、快樂、有公義,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國家。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創造一個公義、有自由、人權的社會,這方面臺灣是很需要的。
撐過磨難考驗
— 鄒秀連訪談紀錄(衛德全的妻子)
(衛:我的後遺症,現在好很多了。太太幫忙很多,好在有她。我很感謝太太,我們家就是靠她。)
我們家有三個兒子、三位媳婦、兩個孫女、一個孫子。我不知道我先生出獄多久,我們才成家,認識的時候他沒有跟我講,結婚前也沒講。
小學曾被衛教過 父親要我嫁他
我們結婚前,我在中壢六和紡織廠上班,小學沒畢業就去工廠工作,就是現在SOGO百貨附近,前後上班十年左右。我的伯母認識他的後母,她們是堂姊妹,那時我媽媽常生病,她跟我媽媽講,我二十二歲可以結婚了。
我小學讀楊梅國校,讀到二年級,媽媽生病就沒有去讀了。我讀一年級時,還是他(衛德全)教的呢。我伯母跟我講,她姊姊有一個兒子,長得還不錯,我伯母沒有跟我講他去過綠島。有一次楊梅有運動會,我從中壢回楊梅,好像十月,有一個妹妹在楊梅國校參加運動會,我就去看看。去的時候,發現有三個人跟著我,我走到哪跟到哪,我就一直躲他們。他知道,我不知道,我想想不對,很害怕。三個男生一直跟著,我趕快走去坐公路局,回去中壢工廠。
(衛:那天是運動會,我們三個人第一次看到她。)
我回到宿舍跟她們講,我說:「我看到三條狼狗。」她們還不知道什麼「狼狗」,她們笑得要死。大家在那裡討論男生怎麼壞,然後她們說:「以後嫁老公喔,絕對不要嫁給當老師的。」沒有錢呀!我在六和紡織工廠,一個月九百多塊,老師才七百多塊。我做紡織工,是做件的,做一碼算多少錢給你。
後來我媽媽生病很嚴重,爸爸一直勸我說:「你媽媽生病,不然她死不瞑目。」叫我一定要嫁給他。我說:「我又沒有看過他。」他是誰啊?我說:「我不要。」教書的人沒有錢,我不要嫁那種人。後來,有一次下班後,伯母叫我去她家,也叫他過來,他沒有進來,在外面等我。他帶我去楊梅國校,這是第一次見面,然後我去坐車回工廠,我九點以前一定要回到宿舍。那次,不記得我們講什麼話,時間很短。之後,跟他見面一次,然後很久沒跟他見面,我不想嫁給老師,但我爸一直催婚。

1994年7月10日,衛德全(第2排右2)與所教的楊梅國小第49屆同學會留影,合照中包括告密的外省老師。(衛德全 提供 /曹欽榮 翻拍)
(衛:第一時間趕,第二是因為我被關十年,跟社會隔絕,看到女孩子就怕。那時候,老人家還有日本時代印象,老師高高在上。)
我在工廠都是上十二小時班,要賺錢養家,每月領錢就拿錢回家。爸爸是耕田的,我有九個兄弟姐妹,我最大,很辛苦。家裡沒有錢啊,只有養豬、養雞賣,連田都沒有水。
還沒有結婚前,我媽生病,每天要回家。結婚前,我沒有真正交過男朋友,我爸爸一直叫我跟他在一起,我當時想:我真的長大了嗎?我怎麼還不知道那個男人一直要追我,我還不懂。到他追我的時候,我才知道。每次回家的時候,他就會在我家的門口站著。
不收聘金 也沒有任何嫁妝
我爸爸認為他很好,雖然他多我十歲,我不會覺得年紀差那麼多,我沒有這麼想。我不想跟他見面,每次我回來,我爸爸一直講那件事情。最後我心裡想:啊算了,這是我的命吧!
(衛:當時想結婚原因很多,我出來沒有工作,心裡還是飄浮,人生沒有目標,能不能娶到老婆不知道,既然有女孩子肯嫁給我,好啦!)
一九六○年十一月,我們就結婚了,他六月才從綠島回來。見面沒有幾次,我們訂婚十二天後就結婚,他怕我反悔吧。爸爸說不用聘金,什麼都不要,他說,拿人家聘金,以後我嫁過去會很可憐。爸爸不買東西,沒有嫁妝,他也不收聘金。
夫妻薪水全交出去 每天餓肚子
我嫁給他半年後,還沒懷孕,因為壓力很重。我每天早上趕六點半的車去上班,回來也都六點半了。天天要回楊梅,同樣回家,你知道我怎麼過日子?我整天過得非常的苦,上夜班也是早上六點半下班,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回到家七點多,還要做家事,做完才能睡覺。他的後母眼睛很大,很恐怖,她不會罵你,她就說:「死貓、死狗,什麼都不會動。」
後來,我六和沒做,改到埔心益新紡織廠,有交通車、也比較近。因為早上不用那麼早,回來不會太晚。那時候楊梅有一條小河,阿兵哥全都在那邊洗澡,下班以後,我要到河邊去洗全家的衣服。家裡有井水,後母不給我洗,她說水不夠用。到河邊洗衣,我很害怕,因為有很多阿兵哥。等到我洗衣服回來,桌上的菜全部吃光光,我還沒吃啊。只剩下湯,碗筷全部在。我一回來,看到後母一眼,臉沒有臭臭,我就添一碗飯拌湯,趕快吃一吃。看臉色不對,我晚上就不敢吃了,只有餓肚子。
我們兩人的薪水要交給後母,我靠一個好朋友,她每月領八、九百塊,她會給我一百塊。她知道我沒有錢。後母不是一般的人,她是專門做老娼,在楊梅車站旁開酒家。
(衛:日治時代,我的養父在車站當站伕,他們在酒家碰到的,養父講客家話,很會賺錢,他什麼都會。後母看到我家房子那麼大,地那麼大,她的目的是要財產。所以我太太嫁過來以後,很可憐,經常要受苦。)
婚後與後母同住 吃盡各種苦頭
結婚住楊梅老家,那時候地還沒賣完,大概剩下一千多坪,四合院的房子。那時候,我不是很會吃苦,我是死愛面子,如果不是愛面子,我早就跑掉了。像那樣的家庭,你能住嗎?看到人家高興就好,不高興連飯都不敢吃啊。我第二天到工廠,他們都知道我今天來一定不對勁,我每天晚上都哭。飯、菜吃光光,剩下湯,我就趕去收一收、洗一洗。
(衛:後母的目的是要苦毒我們,讓我們住不下去,然後把我們趕出去。)
我一年沒有生,後母就跟他講:「沒關係,你把她離掉,我會娶一個給你。」你想想看,那種生活你會生嗎?我這隻手剁到,疤還在,有一條線。她養豬,我要剁豬菜。結婚時,後母送的項鍊我都戴著,有天我先生要去上班,後母叫他脫我的項鍊給她。我很生氣,一直剁豬菜,我想說:為什麼我戴著項鍊要脫走?我爸爸沒有收你們的聘金,什麼都沒有。我就一直剁,亂剁啦,就剁到手,我也不理,就讓它流血,豬菜裡很多血,我就煮好一鍋,煮好我去洗澡。洗完澡,我也不包,讓它流血,看會不會死。所以現在我心裡會想說,我不要讓我的媳婦吃這個苦。

衛德全與鄒秀連結婚時,兩家家族合照。(衛德全 提供 /曹欽榮 翻拍)

衛德全結婚後,最有家庭幸福感的日子,是在三湖國校任教時,一家五口在宿舍前合影。(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結婚第三天就想走 怕丟臉不敢講
我娘家都不知道這些事,講起來我很傻,不知道不能用她(後母)的籃子放要洗的衣服。我去洗衣服回來,要到走廊晾衣服,那時候我怕到連衣服都不會晾,租我們店面賣鞋子的老板娘咬牙跟我講:「晚上你該死!」因為她看到後母把衣服丟在地上。後母竟然跟他(衛德全)講:「你太太很可惡、很不孝,把衣服丟地上,不相信你去看…」。那天晚上,我沒吃,我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天亮。第二天上班眼睛都腫起來了,後來後母跟別人講,說我哭到天亮。她從倉庫那邊偷聽,再繞兩個門出去,你看,這樣的家怎麼住下去啊!
我老實告訴你(指衛德全),我結婚第三天就想要走人。為什麼我沒有走?這是很丟臉的事情,我一直想要跟你講,我不敢講。結婚的那天,是誰弄的我不知道,我進房間還沒有發現,我還不知道,我很笨,我很單純的人,就只在工廠上班。結婚第二天,在睡覺的時候,我婆婆衝進來,我不知道她衝進來要幹什麼?怎麼會有我這麼笨的人?她就跑到我的床上去看,她放了一塊白布在那裡,我不知道咧,那塊白布她拿走了。後來聽我伯母講,她說今天我不是處女,她馬上要叫我走。
你知道她多壞嗎?有一次後母從裡面走出來看到我,人就走掉了,她跑去洗手檯,水打開,把衣服弄得濕濕的,我在看她幹什麼,我想問她:「妳衣服弄到什麼了嗎?」但是我不敢問,我很怕她。他一回來,她就跟他(衛德全)講說:「你看你老婆,是不是外面有客兄啦。」她說是不是我的客兄來了,茶還沒有喝完,當著我的面,說:「你看我的衣服。」我很久以前就想講,我怕傷到他。說什麼魚最毒?鯉魚最毒,人什麼最毒?後母最毒。我生了老大時,後母和她的養女兩母女,站在我的房間跟我講:「你生一個就死一個。」這個話我不曾講過。
被趕出家門 忍辱持家帶小孩
有一次我煮飯,已經生了老大,我想奇怪,飯怎麼有怪味道,有肥皂味,很臭,飯大概不能吃。我想講這飯大概不能吃,她就說:「妳那麼辛苦,就搬出去啊。」她拿一個鍋子、兩個碗給我,鍋子根本不能煮飯,我們就這樣出去什麼都沒有。我們去租學校校工的房子,姓葉的大家族,我們住在他那裡。大家都對我很好,他們全是客家人,那個阿公很好,很早就在學校當校工,後來換他兒子做。在那邊住很久,到我生第兩個孩子,才搬到三湖國校的宿舍,那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後來學校改名瑞原國小,三湖國校是一九二五年建校吧。
那位阿公年老生病時,我去看他好幾次,去看他的時候,他拉著我的手,我坐他的床頭,他牽我的手說:「妳以後會很好,現在辛苦一點沒有關係。」他說:「妳的手掌很厚,以後妳很有福氣。」阿公這樣說:「妳以後不會吃很多苦,你要有耐心。」我知道要忍耐,連我娘家都不知道我過什麼生活,我不曾回去講,講了能怎麼樣?不嫁人不是很好嗎?我沒有這樣想過。只想說,我怕我老公會被我爸爸、媽媽看不起,我會怕。我不要讓人家看不起我老公,說我老公怎樣,家庭怎樣,我不會跟別人講。
為照顧三個孩子 養豬養兔子賣錢
在三湖國校,住了很多年,三個小孩都出生以後,一陣子我沒有上班,我有養豬、養兔子,兔子那時候很貴,可以賣錢。不然,怎麼生活?他一個月那麼少錢。
到小孩要讀書的時候我自己帶,我也去上班,四點半起來做便當,做好叫老大起床,我要出門,五點十分,搭三班車去楊梅上班。能買現在的房子,是一位張老師的老婆幫忙,她問我:「妳現在要不要買房子?」我說:「我沒有錢啊。」她說:「你沒有錢,沒關係,我幫妳打會,讓妳做會頭。」我那時候沒有錢不敢買房子,他(衛德全)在南澳教書,我在楊梅上班,那時候七萬塊買的房子,她幫忙很大。
還沒結婚前,我活得很快樂,雖然我爸爸很沒有錢,可是我很快樂。真的呀。每個月幫忙家裡,我還可以買很多衣服,穿得很漂亮。那時候我認識他,公司要我出國,薪水加兩倍,去外國的工廠教人半年,爸爸卻不讓我去。
結婚後生老大,生活實在不太好,搬出去以後就慢慢好了。慢慢像個家,是搬到宿舍,三湖國校的宿舍住了十年左右。從三湖國校搬出來,他去日本一年,然後回來,搬到水美國小。他說要去日本,然後要帶我們去日本,他是這樣想,在臺灣生活不下去。
先生怕黑恐慌 需陪伴不敢出遠門
(衛:但是臺灣政府不讓我們去,警備總部的人說:「讓你去就很好了,你還要全家搬去。」我是從日本回來以後睡覺才要開燈,我只要有一點亮就可以了,我從來都不敢講。怕她傷心,我自己也傷心。第一個我是擔心家裡,她一個人帶三個孩子,政府又不讓我帶他們出去,那我必須回去,我心裡很亂很亂,天天想到家裡,引起恐慌的心理。她有時候是因為忙啊,很累,孩子要照顧,又要去工作,所以她一下子就睡著了。我有時候沒有睡,她也不知道。我經常還沒有睡著,她已經睡著了。我特別到臺中去看醫生,一位孫醫師,我不敢講說我被關十年,只說我晚上睡不著。)

1971年,衛德全赴日本工作時,至日本皇居二重橋前留影。(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他是我不在家的時候,我三、五天不在家,才會這樣。所以我不太敢出門,很多人找我去哪裡,有時候我就想,一天的可以,像有一次跟朋友去泰國五、六天,回來他跟我講,他開車開到迷路,我嚇死了。
為衛家三個媽媽盡心料理後事
後母本來有糖尿病,她吃藥不會好,就把一隻腳鋸到膝蓋。後母腳鋸掉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我沒有住在那裡,過年過節我會回去拜拜。有一次我回去拜拜,我問她:「媽媽,妳怎麼腳鋸掉?」雖然她那麼討厭我,我看她這樣子不能走,一個人躺在那裡,沒有人照顧她,我也不忍心。我要煮給她吃,每天吃得不一樣,我每天跑回來埔頂。跑回來遇到轉角那家小書店的太太,原本大家不相識,她看我每天這樣跑,有一天,她問我:「為什麼妳每天這樣跑?這麼辛苦,跑什麼?」我說:「我上班,婆婆生病,我要買東西趕回來,還要洗,還要煮。」她說:「妳這樣好辛苦,乾脆我幫妳,多少錢不知道,我去買,妳來付錢,我幫妳洗好,幫妳煮,讓妳輕鬆一點,讓妳好下鍋。」我煮好送去楊梅給她吃,回來都晚上十二點了。
(衛:雖然後母對我、對她真的很可惡,但是我們還是很尊重她,很孝順她。她常常買東西回去給她吃,她的養女說:「就是妳啦,她會早死就是妳…」)
她之前很討厭我,她說:「死了不要給我看到。」你絕對不會相信,所以她死,他(衛德全)沒有看到。我端午節送粽子給她吃,我回去拜拜,煮給她吃。她很高興,跟我說:「我現在沒有錢好給妳。沒有關係,我現在活著,對她(她的養女)沒有辦法,我死了,我還是會把她的錢耙回來給妳。」她這樣跟我講。她死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哭得那麼傷心,那麼難過,我是恨她,還是看她那麼可憐沒人理?她早上出殯,從裡面抬到外面去,沒有一個人在那裡,都是我一個人,哭個不停,我自己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我哭什麼。我只有給她罵,我才會這樣哭,我哭什麼沒有人知道的。
我嫁給他之後,有一次我作夢,他的爸爸我不曾看過,也沒有看過照片,我只有作夢夢到他,晚上睡覺在哭的時候,哭到睡著了,爸爸來跟我講:「妳不要天天在傷心了,我會難過,她(指後母)對我也是這樣子,不是對妳這樣子而已。」他說:我要忍耐。我都不曾講,他叫我要忍耐。
每天下班跑到臺北照顧大媽
我大媽(衛的養母)生病。大媽被後母趕走,離開衛家之後,去幫人家煮飯。大媽去照顧一對老人,一直照顧到兩個老人家都過世,他兒子就把她帶去臺北。後來,她生病了,我在工廠上班,他就打電話到工廠,跟我說我大媽在臺大住院。那時他(衛德全)在日本,我天天下班都要去臺北,你看我三個小孩子都要照顧,我還要跑臺北。差不多不到半年的時間,她就走了,放在殯儀館。第二天,我又去,把後事辦一辦,辦完的時候半夜十二點多,我三個孩子在家,沒有去,那我要怎麼辦?我叫計程車,問計程車司機:「你可不可以載我到楊梅?可是我先跟你講一個條件,我是要載媽媽回家。」司機回說:「可以呀。」我問:「多少錢?」我想一百二,大概是。然後我說;「我媽媽往生了。」司機說:「那妳要包紅包。」紅包一百二,我說好。回去楊梅,我租人家房子,你想我要把帶回來的祭藍吊在哪裡?我大兒子才六年級,把它吊在門口,大兒子說:「阿婆以後就住在這裡,妳要保佑我們。」然後點香,半夜一、二點,三個孩子叫起來,點香拜阿婆。
婆婆往生前為她梳洗打理後事
說到生他(衛德全)的婆婆,生病沒有很久,頭尾只有二十一天就過世,我住在臺北十五天,沒有洗過澡,也沒有洗過臉,沒有一個人去幫我,我每天都在她旁邊,她什麼話都會跟我講。她跟我講說:「榻榻米搬起來,下面有錢。」我不會為了那個錢,大家傷和氣,大家也不知道我婆婆有錢。她跟我講哪裡有戒指、哪裡有一條項鍊。我婆婆往生前,只有我一個人在,我幫她洗完澡,很冷,我就用木炭,弄一盆一盆火。我抱她上去,讓她坐著,幫她洗頭、洗澡。她還沒有死,跟我講說:「有一天我要走的話,妳一定要幫我洗頭髮。」我說:「好,我會的。妳不要講那會嚇人的話,我會很害怕。」我說我膽子很小,不要一直嚇我。她說:「我跟你講真的啦。」她出院回來才往生的,那八千塊我全部交出來給廖家兄弟,連戒指、項鍊,我全部交出來。我二姑還跟我講說:「妳怎麼那麼忠實(客語,老實)啊?不會自己暗藏下來啊?」我說:「我做不到!」
現在他每天早上起來吃早餐,吃完就看他的報紙,剪他的報紙。我一早五點多,就去菜園。他的養姊,住在臺北,也是受日本教育,已經九十六歲了,這位姑姑很疼我。她一直住在美國,現在才回來臺灣住。她每次來都罵我:「什麼事都不給他做,都是妳一個人在做。」我媳婦就跟她姑姑講:「你不知道我媽媽很厲害,我媽媽會做水電,我媽媽會接電,我媽媽會打地,我媽媽什麼都會做。」我看錢不會很重,我現在沒有錢,也過得很快樂,我就傻傻的。
夫妻老來相伴 兒媳孝順生活快樂
我已經七十幾歲了,身體還很健康,像牛一樣,我一天要動三、四次,勞碌命啦。現在每天早上四點半就起床,五點多去菜園澆菜、採菜,採完、挑好,一包一包用報紙捆起來,拿回來放冰箱冰庫,回來洗一次澡,等一下午再去,回來再洗一次澡,晚上洗一次澡。我第二個媳婦會回來煮,現在我不煮了。老大在臺北上班,禮拜六、禮拜天就回來,他還沒有回來前,會打電話說:「爸爸,明天早一點起床。」媳婦會說:「爸爸明天早上幾點吃早餐,我會買回去,我今天要帶你去哪裡…」。
等三個兒子通通高中畢業以後,他爸爸才跟他們講過去被關的事。大的很照顧他兩個弟弟,每個禮拜,他和大媳婦會帶我們出去走走,三個兒子都很孝順就夠了。老二跟老三開的天祥公司,是做清潔維護。孩子雖然沒有大學畢業,但是他們對我們很孝順。小孩子都不用我們操心,反而小孩在操心我們。
另參考︰200 8年「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採訪計畫」。
8年「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採訪計畫」。
錄音轉文字稿:林芳微、曹欽榮
文字稿整理:曹欽榮
修稿:衛德全、曹欽榮
(本文摘自《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歷史文集》,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欲購此書請電洽03-332-2592分機8403邱小姐。)
相關系列:
【重生與愛】系列四 黑夜漫漫無時盡 ― 衛德全訪談紀錄(上)
【重生與愛】系列四 黑夜漫漫無時盡 ― 衛德全訪談紀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