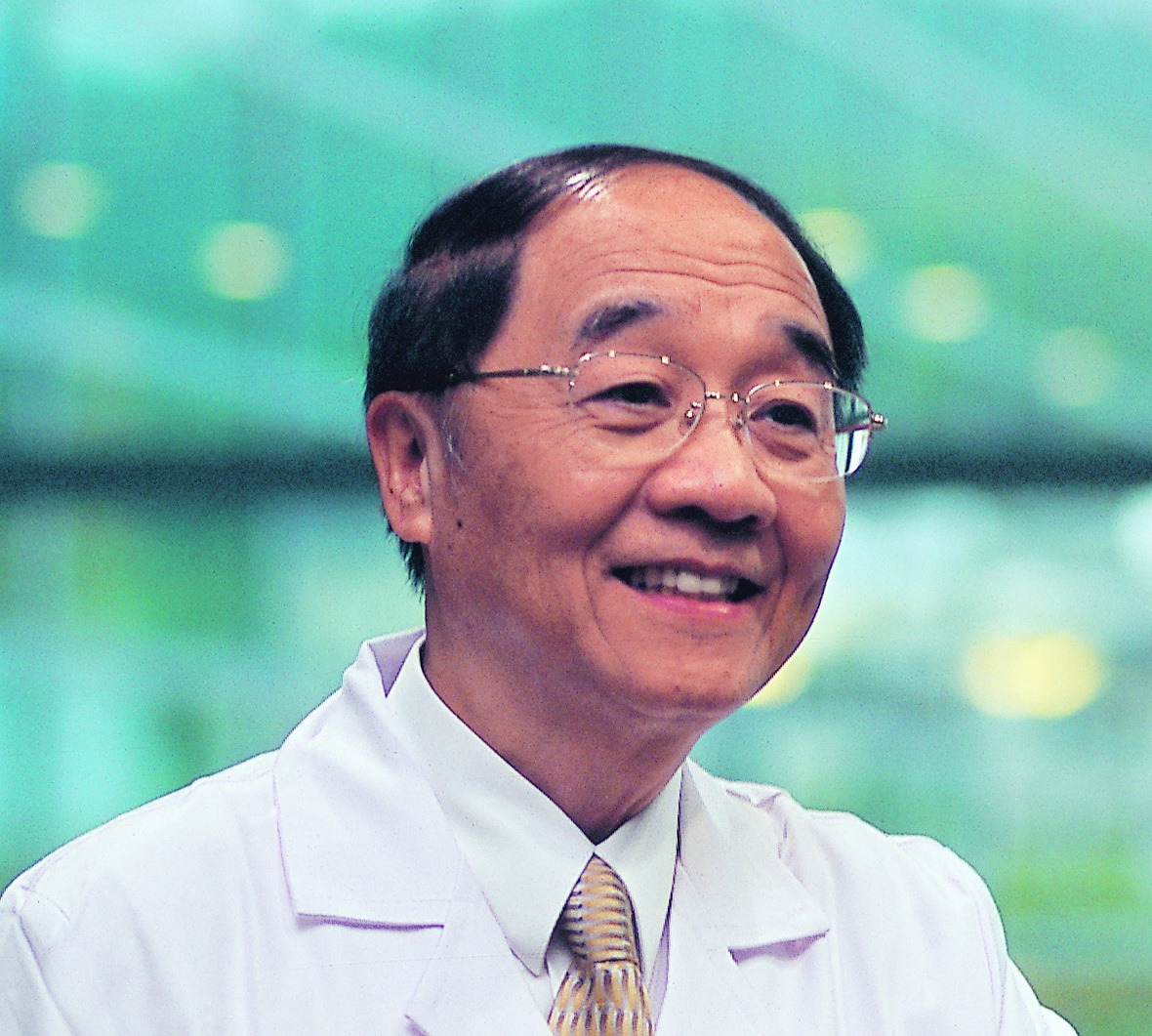上星期六到國外開會,想不到這一星期裡,台灣立法院裡發生了這麼驚天動地的學生運動。更讓我感動得是,一位我曾經教過的醫生以電子信函告訴我,他們一共有五十位醫療人員,主動響應這件「反服貿」學運,而進駐立法院,以保護在這又濕又冷的天氣裡,可能有人需要醫療人員的服務。他並且邀我星期五晚上回台時,由機場直奔會場聲援。他說這些醫療人員真的非常難得,能夠臨時排除萬難,得到工作單位與同事們的配合,身為醫者,我也深知這種離開工作崗位而又不犧牲病人的照顧,一定需要幕後的許多無名英雄的幫忙。
然而很不幸地 我在抵台時發現自己喉嚨痛、聲音沙啞、咳嗽、流鼻水,而不得不在機場打電話告訴這位還在現場的醫生,告訴他我不宜到那麼多人關在立法院裡的環境,萬一有學生因此染上感冒,我深為醫者將難辭其咎。我在電話中表示我非常關心學生們的安全。想不到這位醫師告訴我,這也是他們參加的另一個動機。因為他們都帶了工作上的白袍,而萬一政府動用軍警暴力對付學生時,他們將一起披上白袍站在第一排,相信再蠻橫的政府,也不敢無視身穿白袍的救人專業人員,而又使出當年陳雲林第一次來台時,使用警察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良民。聽了這些話,我開始沉思,難道除了無法去現場向這些醫界有勇氣的一群年輕人打氣以外,我就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嗎?
今天早上我又與這位年輕醫師打了電話,才知道他們非常擔心的是萬一醫師公會對這些可敬的醫療人員發表譴責,是否會引起他們的工作單位對他們開刀,這使我決定至少我需要在這關頭,挺身而出為這些有正義感的年輕醫療人員發聲致敬。
我那天一直目不轉睛地凝視電視,看著他們與江院長條理清楚地表達他們的的心聲,而氣定神寧地站穩立場。突然間,我想到十五年前回國時,我也曾公開地同意醫學院老師們形容年輕一代的醫學生是抗壓性非常低的「草莓族」,而今天我不覺自問,如果時光倒轉四十幾年,我會挺身而出嗎? 我謹在此向這些醫療人員致上最大的敬意,同時我也在此呼籲這些人員所屬的醫院院長能夠給予他們應得的尊敬,因為他們做到了許多我們做不到的「醫師的社會責任」。